不久,我們便收到奧馳亞發來的郵件,向我們索要内部密碼,而他們所有的顧問公司都在轉發人名單裡。奧馳亞的做法與當初戴維的承諾截然不符,這一事實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競標流程。我對他們保護我們不受沖擊的承諾失去了信心,甚至認為這次保密事故反映出了他們的管理層存在的纰漏。戴維對我解釋說:“我還以為那些信息是可以嚴格控制的,以為自己設置了轉發障礙,但卻沒有。也許是某人回郵件時不小心錯點了‘回複全部’,結果讓你們的資料傳到了某個不相關的人手裡,而這個人不知道我們之間有協議,於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讓密碼洩露了出去。”讓我更擔心的是我們的競争對手。為什麼我們的競争對手以及跟它關系密切的招標顧問公司不主動回避這種可能導致雙方利益沖突的尴尬局面?為了避免沖突,他們應該不想知道我們的密碼才對。所有這些疑慮開始互相放大,嚴重影響了我們參與競標的激情。不久,這種疑慮發展成了一種直接對奧馳亞集團的擔憂:奧馳亞的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我開始為這些問題失眠。一方面,我實在沒法開口讓一家《財富》10 強企業呆一邊涼快去,我想接下這單生意,我不希望看到它落到競争者手中。我們是這一行業的佼佼者,我們有能力為其他行業的佼佼者( 比如說奧馳亞) 打造解決方案。我真的相信LRN 會贏得這次競標。但在另一方面,現實情況正在與我的信仰體系中的某些信條產生很深的抵觸。不管奧馳亞的人是否真的把這當做一種沖突來看待,戴維和他的遴選委員好像都不尊重我們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們完全錯了,那兩家顧問公司根本就不應該參與遴選。我們和他們有切實的利益沖突,如果我們要繼續競標,他們就必須讓出道來。於是,我給戴維打電話,表達了這一觀點。我告訴他,盡管奧馳亞並沒意識到我們面臨的利益沖突會對我們的競標資格產生實質影響,但我們已經深深感受到這種影響,沒法繼續在會面時表現出應有的開放度和透明度,沒法繼續坦率地和奧馳亞探讨方案的優點、缺點或是需要改動之處。總之,我們已經沒法繼續向奧馳亞展示出我們實際擁有的能力。
戴維很認真地聽取了我的意見。但他表示,這個問題必須經過集體讨論後才能給我答複,而集體讨論的結果卻是,奧馳亞認為那家顧問公司的存在沒什麼問題,不打算對此採取行動。戴維後來解釋道:“盡管我沒有獨立決策權,但我是合規團隊的頭,而且深信自己能率領團隊公平地完成競標過程。所以,盡管多弗說的一切從理論上講都是正確的,但我覺得,如果LRN 或者其他哪家公司就是最好的方案服務商,那它最後一定可以通過我們的考核。我認為這件事給我的教訓之一是,我們當時的認識竟然如此不同。我相信,也許聽起來有點狂妄,沒有人會因為這種程度的利益沖突就放棄贏得我們公司業務的大好機會。我對奧馳亞的吸引力很有自信,並且認為,不管招標顧問公司和某位競標者之間有什麼樣的利益關系或内幕交流,在我們公司名譽與管理績效的擔保下,大家都應該對我們抱有足夠的信心,應該相信我們會公平地選出最適合奧馳亞的合作夥伴。”
本文摘自《方式決定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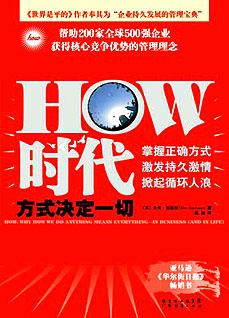
在HOW時代,不僅要“放手去做”,更要“正確的做”“遵從規則”已過時,“超越規則”是殺手锏不僅考慮“能夠做”,還要學會“應該做”
安然、AIG、三鹿奶粉、國美等,接二連三的公司醜聞突然間讓我們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可以說,信息技術催生了“透明文化”,同時也宣告了全新的“HOW時代”的到來。
《HOW時代》提出了颠覆性的觀點:
HOW比WHAT更重要 在透明文化盛行的今天,產品和技術(做什麼)極易被複制,而正確的方式(怎樣做)才最具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