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能規範人的行為嗎
為什麼我們要拿規則當代理?因為規則似乎具有高效性,而現代社會以及整個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礎之上的。比如,絕大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把年齡作為劃分公民投票權的標尺。在美國,18 週歲可以獲得投票權,在日本是20 週歲,其他一些國家可能是21 週歲( 把21 週歲作為獲得投票權的年齡是因為在英國歷史上,這是獲得騎士頭銜的起始年齡。--譯者註)。然而,年齡並不一定如實反映個人的心智發展、思想成熟度,或是社會責任感,恰恰是這些素質可以作為更準確地衡量選舉人資格的標準。
如果你想進行一次社會回報效應最理想的選舉,並使這個選舉給更多人帶來利益,你可能只讓那些成熟的、有公民責任感的人參與投票。但事實上,我們選擇了一個代理參數--年齡--作為心智成熟度與社會參與感的客觀量化標準,希望靠這個武斷的界限能把更多的合格選民包含進去,選出一個可以代表民意的新政府。但事實上有很多人到了25 歲都搞不懂什麼才算是合格的政府,而有的人從15 歲開始便具有了極強的公民責任感。由於採用代理參數,而非直接採用主觀價值作為選民資格評判的標準,我們讓很多本來不夠格參與投票的公民投了票,同時也排除了許多理應參與投票的公民。從這種意義上說,法定選舉年齡等類似規則的範圍總是顯得既過於寬泛又過於狹窄。
如果只允許素質合格的選民投票的話,這無疑是一次理想的選舉。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相反,如果選舉規則只限定於年滿18 週歲便可投票的話,那麼執行起來會簡易許多。你在選民註冊時便可以輕易地確定他們的年齡和公民權;到時候他們帶著註冊證明就可以直接參與投票,這樣在全國大選時間可以控制在一天之内。另外,如果想調查清楚選民的心理成熟度或公民責任感之類的素質,就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最終調查結果可能只是主觀結論。因此,在一個基於規則的社會體系裡,在效率與價值的對比中我們通常會選擇前者。基於規則的社會統治體系一般可以公平地代表大衆的價值,而這一體系所推崇的效率中卻隐藏著一個深層的缺陷:我們深信不疑的規則體系在很多時候並非是達成特定目標的最有效或效率最高的方案。認識到這一缺陷,對於在How 時代取得成功來說非常重要。
規則往往缺乏一個有效率的、系統化的制定機制。規則有的由民選政府制定,但政府往往被手持票倉的政治利益集團控制;有的由掌控政治或軍事權力的野心家制定;還有的由企業主或大公司董事會制定,這些人本身可都是按照精英的標準被挑選出來的。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曾經開玩笑說,他甯願接受波士頓電話號碼簿裡開頭2 000 名陌生人的管理,也不願意呆在哈佛校董會那些看似聰明的人手裡。盡管人們總是出於善意來制定規則,但最終出台的規則卻總免不了要針對種種消極的社會行為。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反複修訂規則,以堵住各種隨著社會環境變化而出現的漏洞。讓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了解這種情況。
本文摘自《方式決定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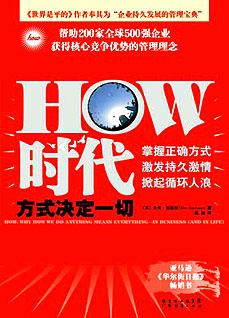
在HOW時代,不僅要“放手去做”,更要“正確的做”“遵從規則”已過時,“超越規則”是殺手锏不僅考慮“能夠做”,還要學會“應該做”
安然、AIG、三鹿奶粉、國美等,接二連三的公司醜聞突然間讓我們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可以說,信息技術催生了“透明文化”,同時也宣告了全新的“HOW時代”的到來。
《HOW時代》提出了颠覆性的觀點:
HOW比WHAT更重要 在透明文化盛行的今天,產品和技術(做什麼)極易被複制,而正確的方式(怎樣做)才最具創造力。